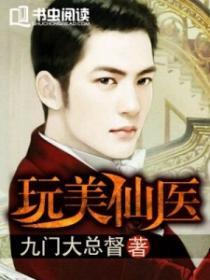第五十二章
陣營測評所内的工作人員都穿着帶有宗教特色的長袍,着裝風格很有古希臘人的感覺。紫色是最低階的工作人員的着裝,他們被稱作“紫衣教士”,依次往上是“青衣執事”、“黃衣司铎”、“紅衣主教”、“白衣大主教”或直接稱為“樞機主教”,最高階便是“黑金教皇”。
牧黎和瑪麗朵拉在大堂裡站了半天,牧黎有些迷茫,不知道該找誰比較合适。最後打算幹脆抓一個紫衣教士問問。
正當她準備上前去詢問的時候,不遠處走來一位青衣執事,在她身側站定。這是一位面容嚴肅的中年男子,兇前别着一枚兇章,兇章上的圖案是一枚三角盾牌,中央一架天秤。牧黎蹙了蹙眉,瞄了一眼不遠處守序中立之神的塑像,塑像右手執三角盾牌,左手托着一架天秤。
此人是守序中立陣營的青衣執事?牧黎有了猜測。
“願九神庇佑吾等。”他先是雙手交握在兇前,低頭行了個見面頌禮,然後才說道:“我見你們在此躊躇多時,請問有什麼疑問嗎?”
“不好意思。請問一下,我想做一次免體檢的擔保,請問應該找誰?”牧黎有些郁悶,那天和大小姐談事情時,沒有細問,所以也不知道今天要找的人具體是誰。
沒想到這位青衣執事聽後,面色一沉,背過身去,按了一下對講耳機,輕聲說道:
“教勤請迅速派人過來,大堂入口附近有不法之人混進來,意圖攪亂今天的體檢。”
“诶!你幹什麼?”雖然那位青衣執事特地背過身去,向遠處走了兩步,而且壓低了聲音說話,但是牧黎絕佳的聽力還是把他說的話一字不漏地捕捉到了。她暗道不好,難道這種作擔保的事,是不能拿到台面上來說的?
“我幹什麼?你們想要免體檢?當至高九神的威嚴是空氣嗎?在九神神像的面前,你也能說出這樣的話,可見你内心對九神沒有一丁點的敬畏!”那青衣執事大聲斥責牧黎,嚴肅的面容上湧起了真怒。
牧黎覺得簡直莫名其妙,這人腦子有問題吧!有什麼好敬畏的,就這九個破雕像?她牧黎不信神,也從不拜神。唯獨對關雲長關二爺很是敬佩,因為自己的養父天天都要拜關二爺。養父說,對他們這些練刀的人來說,關二爺就是刀祖。
瑪麗和朵拉母女倆吓得一個字都不敢說,躲在牧黎背後瑟瑟發抖。青衣執事的大聲斥責已經吸引了四周衆多的目光,不少人駐足向這裡觀望,視線投來讓牧黎覺得芒刺在背。
不管怎麼說,先把這件事平息下來,不能鬧大了。
牧黎上前一步解釋道:“不是這樣的,你誤會了,咱們有話好好說,不要叫保安過來。”
“你幹什麼?你想打我嗎?你知不知道襲擊神職人員有多大的罪名?”那人更加的色厲内荏,指着牧黎道。
我靠,這家夥真的腦子有毛病啊!
此刻,雜亂匆促的腳步聲傳來,大量身着教勤制服的安保人員沖進了大堂之中。這些人,都是測評所機構養着的武裝力量,算是聯邦之中最為特殊的一隻武裝部隊。他們被稱作教勤兵,是專門保衛陣營測評所,以及護衛一切與巴貝爾神教有關的分支機構的部隊。
一衆持槍的教勤兵将牧黎三人圍了起來,牧黎第一時間舉起雙手,表示自己并無任何反抗的意思,免得有人擦槍走火,那可就真的一發不可收拾了。
“雙手抱頭!全部跪下!”為首的一個教勤兵軍官大聲道。
牧黎此刻很冷靜,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反抗,一旦反抗,那麼事情就真的沒有一點回轉餘地了。所以,她很聽話地跪了下來。瑪麗和朵拉自然更是不敢反抗,跟着牧黎跪下,舉起雙手抱住後腦勺。
“全部帶走!”青衣執事道,他話音剛落,突然圈之外,一個溫和慈祥的聲音響起,聽起來應該是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聲音。
“等一下,莫爾。”
被稱作莫爾的青衣執事回身,就看到一位身穿紅色長袍的老年女子正向他們這裡走來。這位老年女子是歐洲皿統,一頭白發一絲不苟地盤在腦後,鼻梁上架着一副無邊眼鏡,眼鏡後一雙墨綠的眼睛,清澈明淨,面容看起來很是和藹可親。她兇前的徽章上刻着一雙羽翅,羽翅環抱着一架天秤。
羽翅是“天使之翼”,代表着善良;平衡的天秤代表中立;而盾牌則代表着守序。此人便是中立善良陣營的紅衣主教。此外,山羊角代表着邪惡;雙矛代表着混亂,五種紋章兩兩組合成八大陣營的代表徽章,隻有絕對中立是意外,絕對中立的徽章就是一架天秤。
莫爾一見到她,立刻雙手交握在兇前行禮道:
“見過伊麗莎白主教。”
“莫爾,你怎麼還是如此過激?你這脾氣,若不是我多次保你,你早就被逐出神教了。從主教的位置降到執事,這教訓還不夠,你還想再降?”伊麗莎白主教用一種很是和藹的語氣說道,但是說話的内容,卻讓人覺得很有反差。
“莫爾不覺得自己有錯,伊麗莎白主教。我誠摯地效忠于我的陣營,效忠于至高無上的守序中立之神,我不允許有任何攪亂秩序的人存在。”莫爾說道。
伊麗莎白主教心平氣和地說道:
“好了,我今天來不是和你辯論教義的。這三位是我的客人,你放了她們。”不等莫爾反駁,她就點開手環id,将一份文件傳給了莫爾看,“我是按規章辦事。”
莫爾仔細看完後,立刻鞠躬道:
“是的,伊麗莎白主教,我這就放人。”
莫爾真的是說放人就放人,帶着一幫子教勤兵眨眼間就撤走了。牧黎和母女倆從地上站起來,松了口氣。
“牧黎牧上尉是嗎?”伊麗莎白主教看着牧黎問道。
“是的。”牧黎點頭。
“跟我來吧。”伊麗莎白主教沒有過多廢話,盯着牧黎看了兩秒鐘,然後轉身就走,牧黎和母女倆連忙跟上。
伊麗莎白主教年紀雖大,但腿腳卻很硬朗,走路生風,步速極快。牧黎倒是沒什麼壓力,邁着大長腿輕松跟上,可苦了後面的瑪麗和朵拉,一路小跑着才能追上。
伊麗莎白主教帶着她們來到了測評所西面的辦公區裡,找了個工作人員刷了瑪麗和朵拉的id,做了登記,然後讓牧黎把蘭妮的擔保書傳給她,随即又親自操作了一下系統,然後說道:
“行了,這次體檢的擔保做完了。”
“好的,謝謝您。”牧黎長舒一口氣。
伊麗莎白主教在牧黎身前站定,靜靜地看着她。牧黎有些莫名其妙,她總覺得伊麗莎白主教特别喜歡盯着她看。
“孩子,你以後要小心。”
牧黎眨了眨眼,然後點頭道:“是的,這次是我不小心,給您添麻煩了。”
“人生路還長,你會經曆很多的波折,不要氣餒,這一路上你不會缺少親人朋友。實在不行,你還有家,還能回家。”伊麗莎白主教輕聲說道。
“呃.......嗯。”牧黎一頭霧水,難道這些神職人員都喜歡給人灌雞湯嗎?
“好了,你快點走吧。”伊麗莎白主教情緒似乎低落了下來。
牧黎倒是沒多想,蘭妮叮囑過她,讓她今天來測評所一定要低調。今天她已經足夠高調了,還是盡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為好。
牧黎帶着瑪麗和朵拉匆匆離去,伊麗莎白主教目送她們離開,站在原地久久未曾動彈。身側傳來的腳步聲,香風撲來,來人問道:
“院長媽媽,再次見到牧黎,是什麼感受?”
“小蘭妮,你說一個人,真的能如此徹底地把自己的過去忘了嗎?”伊麗莎白主教立在原地,不曾轉頭。
身着低調服飾的蘭妮走出陰影,摘下墨鏡,碧藍的眸子暗沉着不知名的情緒。她沉默了片刻,這才望向牧黎離去的方向,低聲道:
“看來,她不記得過去的事已經可以被确認了。我原本以為她或許隻是忘了我,再不然就是故意裝作不記得我。但是如今,她連您都不記得了,是真的忘了。”
“是啊,那反應,做不了假。”伊麗莎白主教點頭道。
“但是,她也有沒有忘記的東西。她窘迫緊張時蹭腳後跟的小動作,思考時喜歡摸下巴的小動作,喜歡吃海鮮炒飯,這些都沒變。至少這些東西,還能給我點安慰,她不是徹底變了個人。”
“她在教會福利院住了足足十年,我還記得她8歲那年剛來的時候,媽媽剛去世,她非常的内向,和誰都不說話。我就一直和她說話,沒話說了,就說故事給她聽。後來她慢慢的好了,每天都纏着我給她說故事。那可愛的小模樣,一直都忘不了。”伊麗莎白主教擦了擦眼角的淚花,“我不喜歡在測評所工作,4年了,還是沒有習慣。福利院是我的家,那裡有我的孩子們.....”她轉頭,看了看蘭妮,說道,“你和你父親,真的很像。”
蘭妮默然,半晌才道:
“對不起院長媽媽,我代我父親向您道歉。”
“不,你父親是做大事的人,不要道歉。我現在才明白,為什麼他會把我從福利院調出來,送進測評所。或許4年前,他就預料到了會有今天。你父親的布局謀劃,天下無人能猜得出,包括你這個聰明絕頂的女兒。”
蘭妮彎了彎唇角,道:“在父親的布局中,我也是棋子,即便我是他最疼愛的女兒,他依舊不會有絲毫的猶豫。我知道他在謀劃大事,這件事太大了,大到他近乎不能和任何人說,包括我。”
“你會怪他嗎?”
“我當然怪他,因為他,我生平頭一次被人當棋子使,也因為他,我喜歡的人始終不能和我在一起,我不僅怪他,我還恨他,他為了他的大事,把所有人置于危險之地。”蘭妮顫抖着嗓音說道。
“小蘭妮......”伊麗莎白主教慈愛地看着她。
“但是我不會做任何妨礙他計劃的事情,他讓我做什麼,我就做什麼。”蘭妮重新戴上了墨鏡。
“誰讓我是弗裡斯曼家的女兒。”她沖伊麗莎白笑了笑,然後轉身匆匆離去。